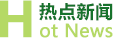公域(common)一词起源于英国圈地运动前大量存在的资源共享的“公地”(common land)。公域中的共享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的特征是:由于成本特别高,很难或者不可能进行排他性使用。由于公地资源可以竞争使用,容易造成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破坏,发生“公地悲剧”。联合国环境署把“全球公域”界定为“处于国家管辖之外的资源或区域”。国际法一般把公海(水体和海底)、大气层、南极和外空视为全球公域。对于网络空间是否属于“全球公域”尚存争议。
全球公域具有以下的特点:
- 无主性,不为任何个人、组织或国家所单独占有或管辖,经济、环境、法律与安全各维度所涉及的资源、领域与区域均系主权国家之外的“无主物”;
- 非排他性,任何个人、组织或国家对全球公域利益的享用不应妨碍其他个人、组织或国家的同等利益,所有国际行为主体负有同等的进入、使用与保护的权利与义务;
- 公共性,全球公域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其所涉及的资源、区域或领域必然具有公共使用价值,与全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根本福祉紧密相连,能够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
- 联动性,其所引起跨国的“公益问题”或“公害问题”必然要通过多边协商才能得到解决。全球公域的资源开发与污染防治等问题都要靠协商建立的国际机制网络实现有效治理。特别是包括国际条约在内的法律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被确认为全球公域,就要被纳入全球议程,受国际法约束。(王义桅等)
目前全球公域的治理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种是以“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来指导、强调一旦开发利益全人类共享的形态,例如公海海底和外空;一种是“为和平的目的而保护”的形式,例如南极;第三种形态是“各自开发、共同保护”,例如公海的生物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断融入和综合实力的上升,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全球的关联度不断提升。这种关联度的提升部分体现在中国参与的多边条约的广度上。1979年以前,中国参与的多边条约一共34个,2007年一年加入的多边条约就达到了18个,2016年一年加入的多边条约也达到了15个,内容涉及贸易、安全、能源、环境等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奋发有为” 成为对中国外交活动的新要求。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提出了“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体现出了对于全球公域问题的关注。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说明了中国外交越来越注重人类共同的利益。
对于全球公域治理问题,国内现有的以“公域”为关键字的研究,大多是从安全角度出发。而例如气候变化这类属于“人类共同关切”性质的全球环境问题,尽管对于相关的国际制度也有很多研究,在以“公域”为关键字的研究中缺很少被提及。实际上如果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关切”,那全球扩散的污染物的排放空间自然就具有全球公域的性质。
因为无主性和公共性,与其他议题相比,全球公域的议题所涉及的利益和参与方是最广泛的。也因为牵涉到全人类的利益,所以在参与讨论的时候需要更加注重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的平衡,或者说利益与道义的平衡。也因为在公域问题上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可能有很大的交集,因此实现多方共赢的可能性也越大。近年来中美关系在一些经济和安全的问题上分歧较大,气候变化和海洋保护方面的合作就成为了中美关系的亮点,特别是中美气候合作为《巴黎气候协定》的达成提供了强劲的推力。这说明公域问题也可以成为政治上存在一定分歧的国家关系的润滑剂。在这种国家并非利益针锋相对的场合的沟通,也可以为其他更加敏感的议题的讨论积累信任。
作为公域的海洋可以从两层意思来理解。首先是狭义的海洋公域,就是指国家管辖以外的海域,也就是公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了国家确定对海洋的管辖权的规则,在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海域就是公海。另一层含义是广义的公域概念,基于贸易的观点,马汉在其《海权论》中他把全球海洋描述为“一条广阔的高速公路,一个宽广的公域”;从生态圈的观点,氧气、水资源、气候等这些生物生存的基本条件又都是与海洋紧密相连。海洋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支柱之一,是人类的共同关切,不论水域是否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内。我们工作的对象虽然是狭义的海洋公域,但是在思考海洋的时候不能因此脱离其广义的含义。
海洋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个体使用者的过度使用导致共有资产退化,从而使个体使用者自身的长期利益受损。这种悲剧的显著特点就是造成损害的人没有承担损害的全部成本。渔业是最明显的。不仅如此,外来物种随着人类活动在世界各地传播,其中对海洋的伤害每年超过一千亿美元。农夫把过量的肥料倒入河流,这些肥料顺着河流流入大海,海上的蓝藻遇到这些养料就会疯长,含氧量随之下降,其他海洋生物就会窒息。2008年,在世界的各大洋上出现了超过400个这样的死亡区。二氧化碳溶解于海水中,产生了碳酸。在此作用下,海洋的酸度自工业革命以来上升了四分之一。在2012年,科学家在南大洋发现有一种海蜗牛的贝壳已经被部分溶解。
有时候可以通过分配私有产权来保护公地,因为这样可以让使用者更加在意这块区域的长期健康。这在沿岸国和岛国的专属经济区得到了尝试。但是这没有在公海得到应用。根据国际法,公海的渔业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而矿产则属于“人类共同遗产”。在这里,国际规则和机构的大杂烩决定着这些公共水域的情况。
公海并不是毫无治理。几乎所有国家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据1980年代的海洋法公约的主席提米.考所言,这就是“海洋的宪法”。其为从军事行动,领土争议(例如南中国海的争议)到 航运,深海矿业和渔业活动制定了规则、虽然其仅仅在1994年才正式生效,但是其包含了几世纪以来的海关法,其中包括海上自由,也就是说公海对所有人开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花费了几十年的谈判,现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美国拒绝签署此项公约,它也遵守其条款。
但是UNCLOS有严重的缺陷:它对于养护和环境的条款很弱。因为它是在1970年代谈判的,在那个时代资源养护的议题几乎不被考虑。而且它也没有执行或惩罚的效力。美国的拒签让问题更加糟糕:虽然它自己的行为遵照海洋法公约,但是他很难去推动别的国家来效法他。
为了监督条约的一些部分一些专业的机构被建立起来。例如规制公海采矿的国际海底管理局。但是国际海洋法公约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各成员国和现有的组织来进行监督和执行。结果就是“九龙治水”,全球海洋委员会称之为“制度化的灾难”。
最大的失败还是在渔业的管制上。公海上三分之二的渔业存量被过度捕捞,这是国家管控海域的两倍。非法和不汇报的捕捞的价值达到每年100至24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渔业产值的四分之一。据世界银行所言,对渔业的不当管理导致了每年500亿美元的损失,这意味着如果合理管理,渔业通过效率提高可以获得至少这些利润。
过度捕捞给海洋带来的伤害比其他所有的人类活动加在一起都大。理论上,公海的渔业是在一系列区域性的机构的管制下,其中一些是针对个别物种的,例如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有些则覆盖特定的区域,例如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他们决定一片海域哪些渔具可以使用,设置捕捞限额,作业船只限额等等诸如此类。但是大多数区域渔业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打击非法渔民。他们不知道有多少渔船在他们的海域,因为目前还没有全球的渔船注册机构。这些组织的规则只对其成员具有约束效力,外来者可以破坏规则却不受到惩罚。粮农组织FAO的一份调查发现汇报在公海监督和执法的国家超过一半声称他们无法管控悬挂他们国旗的船只。即使他们愿意这么做,到底区域渔业组织或个别国家能有多大作为也很难说。
除了渔业,公海生物资源治理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公海中的海洋基因资源。对这一资源的关注起源于公海海底热液喷泉的发现。在上个世纪70年代联合国谈判《海洋法公约》的时候,主流科学认为深海的海底没有阳光,水压巨大,并不适合生物生存,是一篇荒漠。因此,《海洋法公约》把公海海底“区域”,也就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底土的资源定义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时候把“资源”限定为“固体、液体或气体矿物资源,其中包括多金属结核”。把这些资源定义为“人类共同遗产”意味着未来开发这种资源的时候,利益需要通过某种机制与全人类分享。我国最近颁布的《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针对的就是这些资源。
但是随着深潜技术的发展,人类发现在深海海底存在着有“海底烟囱”之称的热液喷口,海水经过地热加热后喷涌而出,而在热液喷口附近居然生存着大量未知的生命体!这些生命体不依靠太阳,仅仅依靠海底的热能和化学能就可以存活下来。这些高温高压下独特的生理特性被视为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因而迅速成为各国海洋科学研究的热点。如果国际海洋法不对此作出任何安排,最终出现的情况就是技术先进的国家和企业抢先将深海基因资源的应用注册为专利,并将其产品化获得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则会被排除在这些利润的分享之外。
根据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为了避免公地悲剧,需要给所有有权利使用的人在运营上有发言权,在有权利和无权利的人之间划清界限,指定受使用者信任的监督者,并且使用直接的手段来解决冲突。而目前的情况时,公海的治理没能满足上述任何一个条件。
近年来,海洋保护逐渐成为国际环境政治中的热点议题,海洋保护不仅被列入了联合国2030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内,海洋议题也被要求加入到气候变化的讨论日程中。2017年联合国召开了首次海洋大会,推动为扭转海洋衰退的趋势做出了自愿承诺。在这些进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历经10年的工作组会议和2年的预备委员会会议后,联合国大会决定在2018年正式启动《海洋法公约》下关于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BBNJ)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政府间谈判了。
在经历了十年的讨论后,联大下设的针对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特设工作组在2015年达成协议,认为需要在《海洋法公约》下设立一个新的条约来管理公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新的条约需要政府间开展正式的谈判,在正式的谈判开始之前,在2016-17年一共召开了两次预备会,会议按照既定的授权,通过了递交给联合国大会(UNGA)的建议,其中包括建议启动针对此文书的正式政府间谈判,也包括了针对此文书内容上的的相关建议。在2017年12月25日,联大就此问题通过决议,决定在2018年正式启动针对该协议的政府间谈判。
BBNJ协议的主要内容基于的是2011年联大特设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向联大提交的建议中提出的作为“一揽子”的四大议题:1)海洋基因资源(MGRs),包括利益分享的问题;2)环境影响评价;3)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4)能力建设与海洋技术转让。不同的谈判集团对这几个议题的侧重并不相同,区划管理工具和海洋保护区是欧盟试图推进的议题,而海洋基因资源则是发展中国家希望推进的议题,将这两个议题一起放在一揽子议题中应该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创绿研究院自2012年开展南极海洋保护的工作,对公海的关注也是由此开始,2015年开始关注BBNJ的进程,主要还是针对海洋保护区/划区管理工具。创绿认为,要对这些国际进程做出实质性贡献,各国需要处理好以下这几点矛盾:
- 经济增长、人民生活需要和过度渔业开发之间的矛盾。研究证明,从长远来看,海洋禁捕区有助于回复海洋的生产力,是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但是在短期内,如何通过使用公共资源解决禁渔导致的社会问题,如失业,是当前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 科学数据的有限性和大规模保护的紧迫性之间的矛盾。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approach)认为,如果对严重、不可逆的生态系统的风险有合理的怀疑,不能以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为理由阻碍成本有效的保护措施。如何基于有限的科学作出审慎的决策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雄心高涨与实际能投入使用的公共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海洋的面积巨大,渔船数量众多,生态系统也在变化,有效的管理和高质量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持。大规模保护区的设置对配套的管理和科研工作提出了更多、更高的的要求。
- 传统上的东西矛盾,或者说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矛盾。彼此的不信任感依然存在,需要通过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解决。
海洋公域是人类共有共管的区域,是应用“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佳舞台。各方也都在期待这些理念在具体技术方案中的体现。中国需要加大对促进科学和政策之间相互协作的投入,同时正确把握进程中“观点的水位”,坚持关注和探讨实际问题而避免原则上的争论,并且努力推进海洋公域生物资源保护政策上的国际合作。